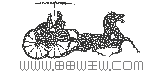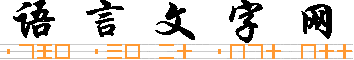韩非的学说,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国末年,诞生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夕。他在《亡征》一文中,列举了四十六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,最后下结论道:“亡征者,非曰必亡,言其可亡也。……木之折也,必通蠹;墙之坏也,必通隙。然木虽蠹,无疾风不折;墙虽坏,无大雨不坏。万乘之主,有能服术行法,以为亡征风雨者,其兼天下不难矣。”
这一段话,应当是他对战国末年各诸侯国政治形势的分析,好像就是专门说给秦王听的。
(一)
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记载:
韩非者,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,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,不能道说,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,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非见韩之削弱,数以书谏韩王,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,执势以御其臣下,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,反举浮淫之蠹,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,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,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,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,观往者得失之变,故作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馀万言。
然韩非知说之难,为《说难》书甚具,终死于秦,不能自脱。……
人或传其书至秦,秦王见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之书,曰: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,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
李斯曰:“此韩非所著书也。”
秦因急攻韩。韩王始不用非,及急,乃遣非至秦。秦王悦之,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。毁之曰:“韩非,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,非终为韩,不为秦,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,久留而归之,此自遗患也,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
秦王以为然,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,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,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,使人赦之,非已死矣。
就韩非个人来说,这确实是历史的误会。大水冲了龙王庙,自家人不认自家人。这个不幸的遭遇,也许跟他口吃、能写不能说有关,他的“说难”,竟成谶语。不过,秦王虽然误杀了韩非,但其后来的行动,表明他接受了韩非的学说。
(二)
“万乘之主,有能服术行法,以为亡征风雨者,其兼天下不难矣。”万乘之主,服术行法,兼天下,这是韩非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,所提出的任务,也是韩非学说的中心所在。
在当时战国七雄中,有哪一个国家具备兼天下的条件呢?看来他已心中有数。他说:“彼明法则忠臣劝,罚必则邪臣止。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,秦是也。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、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,山东是也。”(《饰邪》)他不仅提出了任务,也考虑到实际情况,明确指出,只有秦国具有兼天下的条件。
韩非是韩国的公子,自然他首先希望韩国具备这个条件。他曾多次建议韩王变法,始终未被采纳。后来他为韩王出使秦国,劝说秦王不要先灭韩(这点或许正好成为李斯陷害他的借口),这表明他已意识到秦王兼天下的趋势不可避免,仅仅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最后来处理韩国的问题,即:“韩可以移书定也。”(《存韩》)
因此可以说,韩非已经预见到秦将统一中国。秦王在读到韩非的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后,竟然说出:“寡人得见此人,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可见正中下怀。而见了之后,却又将他杀害。秦王统一中国,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以后,不久又分崩离析,土崩瓦解。韩非的命运,和秦朝的兴衰,也预示着法家学说的价值,和隐含的巨大缺陷。
(三)
万乘之主,服术行法,兼天下,这话可以这样理解:大
所谓法,就是政策法令。“法者,宪令著于官府,刑罚必于民心。赏存乎慎法,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此臣之所师也。”(《定法》)“赏莫如厚而信,使民利之;罚莫如重而必,使民畏之。”(《五蠹》)法令由官吏执行,具体措施就是厚赏重罚。
韩非的法,从内容上看,主要是鼓励耕战,他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根本。韩非并没有为未来的帝国草拟出具体法律,这是因为他没有亲自执政,同时也由于商鞅在秦孝公时实行变法,在实践中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韩非对于商鞅变法,从根本上是肯定的,但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。
“公孙鞅之治秦也,设告相坐而责其实,连什伍而同其罪。赏厚而信,刑重而必。是以其民劳而不休,逐敌危而不却,故其国富而兵强。然而无术以知奸,则以其富强也,资人臣而已矣。……故战胜则大臣尊,益地则私封立,主无术以知奸也。商君虽十饰其法,人臣反用其资。”(《定法》)
商鞅变法使秦国“国富而兵强”,这是韩非所肯定的。但是“主无术以知奸”,这样,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果,往往被大臣们所篡夺,这是韩非所否定的。这个评价是否恰如其份,暂且不论,但表明了一个观点,他认为法与术要结合起来。
所谓术,就是君主的权术。“术者,因任而授官,循名而责实,操生杀之柄,课群臣之能者也。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(《定法》)这里的所谓术,是指君主选用官吏,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的统治策略。举例来说:
韩昭侯使骑于县,使者报。昭侯问曰:“何见也?”
对曰:“无所见也。”
昭侯曰:“虽然,何见。”
曰:“南门之外,有黄犊食苗道左者。”
昭侯谓使者:“毋敢泄吾所问于汝。”乃下令曰:“当苗时,禁牛马入人田中,固有令,而吏不以为事,牛马甚多入人园中。亟举其数上之。不得,将重其罪。”于是三乡举而上之。
昭侯曰:“未尽也。”
复往审之,乃得南门之外黄犊。吏以为昭侯明察,皆悚惧其所,不敢为非。
这是《内储说上》的一则小故事,叙述韩昭侯用术来检查法的执行情况。韩昭侯并没有亲自实地观察,而他让官吏感到他对情况了如指掌,不敢弄虚作假,这样就可以驾驭群臣。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,申不害就是专门提倡术的。不过,韩非对申不害也有所批判。他说:“申不害,韩昭侯之佐也。韩者,晋之别国也。晋之故法未息,而韩之新法又生。先君之令未收,而
申不害单纯的强调用术,而忽视了法令的统一。术和法不结合起来,就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韩非的结论是:“君无术则弊于上,臣无法则乱于下。此不可一无,皆帝王之具也。”法与术缺一不可。
法和术的区别是:“法者,编著之图籍,设之于官府,而布之于百姓也。术者,藏之于胸中,以偶众端,而潜御群臣者也。故法莫如显,而术不欲见。是以明主言法,则境内卑贱莫不闻也;用术,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。”(《难三》)
法要人人遵守,所以是公开的;术是君主胸中的心机,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昭侯谓使者:“毋敢泄吾所问于汝。”就是要他保密,不让人知道。三国时期的曹操,也常常使用这种权术。
要服术行法,就必须有势的支撑。没有势的支撑,法也难以推行,术也无法使用。所谓势,就是君主的权威,亦即帝位。法术势这三者,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呢?韩非之前的慎到,是偏好言势的。他说:
“飞龙乘云,腾蛇游雾,云罢雾霁,而龙蛇与螾蚁同矣,则失其所乘也。贤人而诎于不肖者,则权轻位卑也。不肖而能服于贤者,则权重位尊也。尧为匹夫,不能治三人,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。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,而贤智不足慕也。”
慎到把势位提到决定性的程度,韩非肯定了势的重要,但并不赞同慎到的观点。他说:“夫有材而无势,虽贤不能制不肖。立尺材于高山之上,则临十仞之溪,材非加长也,位高也。桀为天子,能制天下,非贤也,势重也。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,非不肖也,位卑也。千斤得船则浮,锱铢失船则沉,非千斤轻而锱铢重也,有势与无势也。”(《功名》)
这一段话,说明韩非充分认识到势的重要。但有了势,不等于有了治。他针对慎到的话分析道:“飞龙乘云,腾蛇游雾,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。虽然,夫释贤而专任势,足以为治乎?则吾不得见也。夫有云雾之势,而能乘游者,龙蛇之材美也。今云盛而螾不能乘也,雾浓蚁不能游也,夫有盛云浓雾而不能乘游者,螾蚁之材薄也。”韩非还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,不服术行法,有了势也可能失去,君主可能成为阶下囚。因此,他认为“抱法处势则治,背法去势则乱。”(《难势》)他还是强调法治,君主需要有材,掌握着法律的武器,再使用权术,那就会万无一失了。
韩非对于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的思想,有所继承,也有所批判。他提出处势,服术,行法,使法术势相结合,而“以法为本”。(《饰邪》)“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,圣人执要,四方来效”,这就是韩非为未来的中央集权帝国,规划的蓝图。
(四)
韩非以法为中心,把法术势结合起来,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。不仅如此,他还进一步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化,与老子哲学挂钩。他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,而是作了根本性的改造。
老子的道,是产生万物的绝对精神,是“万物之宗”,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。韩非把老子的道,改造成“法”,成为客观规律性的东西。韩非说:“道者,万物之所然也,万理之所稽也。” “短长、大小、方圆、轻重、白黑之谓理。……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,则万物之功形矣。而万物莫不有规矩。”(《解老》)这里他把道解释成万物万理的规矩,万物万理的规矩,也就是规律,也就是法。他又说:“安国之法,荒饥而食,寒而衣,不令而自然。”这个法,也就等同于自然之道。这样就把“道”与“法”联系在一起了。他又进一步解释道:“稽万物之理,故不得不化。不得不化,故无常操。无常操,是以死生气禀焉,万智斟酌焉,万事兴废焉。”这就为变法找到了理论根据。
老子提倡无为,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。韩非把无为改造
韩非认为君主只要用术来驾驭群臣就行了,无须自己亲自动手干这干那。“物者有所宜,材者有所施,各处其宜,故上下无为。”(《扬权》)这无为的意思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,别狗拿耗子。也就是唐代魏征所说的“垂拱而治”。韩非对于无为而治的解释,倒有限制君权的含义,但是,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
老子主张“守静笃”,韩非把它改造成“处势”。他说:“人主之道,静退以为宝。不自操事,而知拙与巧,不自计虑,而知福与咎。”(《主道》)这就是“处势行术”。“制在己曰重,不离曰静。重则能使轻,静则能使躁。故曰:重为轻根,静为躁君。故曰: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。邦者,人君之辎重也。”(《喻老》)守静笃,就是要君主牢牢地掌握着辎重,掌握着“位势”。
老子的道、无为、守静笃,在韩非的笔下,就成了行法、服术、处势。他改造了老子的哲学,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中央集权思想,寻找到理论根据。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,伸张它的合理和正义。
(五)
韩非的法,与孔子的礼,不能说没有关系,礼其实也是法。不过孔子提倡的礼,是恢复西周的礼,而韩非所说的法,是要变法。二者是完全对立的。
孔子说:“周鉴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“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。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
韩非说:“古今异俗,新故异备。” “故事因于世,而备适于事。世异则事异,事异则备变。”(《五蠹》)“时移而治不易者,乱。”(《心度》)“国无常强,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,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(《有度》)他认为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,处理方法也要跟着改变。变法能够富国强兵,不变则会处于弱国的地位。
孔子提倡“仁”,孟子提倡“义”,他们想培养一批有仁义道德的君子,成为官员来执政,以便改变社会的风气。对于军事经济,则较为轻视。
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‘俎豆之事,则尝闻之矣;军旅之事,未尝学也。’明日遂行。”(《卫灵公》)
“子贡问政。子曰:‘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’子贡曰:‘必不得已而去,于斯三者何先?’曰:‘去兵。’子贡曰:‘必不得已而去,于斯二者何先?’曰:‘去食。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。’”(《颜渊》)
孔子虽然提到了足食足兵,而却把信誉放在首位。孔子还把想要学习农业的樊迟,斥责为小人,极度轻视农业生产。这就使得他想要培
韩非则相反。他认为“当今争于气力。”(《五蠹》)他像商鞅一样,提倡“耕战”,要使“游食之民”“归农”。他异常激愤地说:“耕者则重税,学士则多赏”,“国平则养儒侠,难至则用介士,所养非所用,所用非所养。”(《显学》)因而主张:“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他看重实际才能,和实际经验,而不是“学而优则仕”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,儒家首当其冲,成为焚书坑儒的对象,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比较起来,儒家偏于守成,法家偏于创新。儒家看重上层建筑(文化遗产),法家看重经济基础。一个社会的进步,首要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。法家重视耕战,也就是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,无疑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。但韩非学说也有一个弱点,那就是怎么样才
(六)
韩非对法术势的论述,看起来全面而系统,但这个弱点却是致命性的。法,本来有限制君权的含义,无论贵贱,都得守法,自然也应该
这一个弱点,韩非自己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。他写了《难言》,《说难》等篇,简直是忧心忡忡。为了要说服君主服术行法,他不仅担心不
凡当涂者(君主身边的亲信)之于人主也,希不信爱也,又且习故。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,固其所自进也。官爵贵重,朋党又众,而一国为之讼。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,非有所信爱之亲,习故之泽也,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,是与人主相反也。处势卑贱,无党孤特。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,其数不胜也。以新旅与习故争,其数不胜也。以反主意与同好争,其数不胜也。以轻贱与贵重争,其数不胜也。以一日与一国争,其数不胜也。法术之士,操五不胜之势,以岁数而不得见。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,而旦暮独说于前。故法术之士,奚道得进,而人主奚道得悟乎?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,法术之士焉得不危!
其可以罪过诬者,以公法而诛之。其不可被以罪过者,以私剑而穷之。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,不僇于吏诛,必死于私剑矣。
他这些话也并非杞人忧天。在他之前,吴起在楚国,因为推行法制,而被宗室大臣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旁。商鞅在秦国变法,秦孝公一死,商鞅也被宗室大臣车裂。这些血淋淋的事件,韩非焉能无动于衷?他已经预见到了前途的艰难,很像是慷慨悲歌。他的“说难”,也就成了他的墓志铭。
经过焚书坑儒,秦朝灭亡的巨大变动,汉朝统治者似乎有所醒悟,终于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但这一儒术,已经“霸王道杂之”,以德为主,以刑为辅,儒法合流了。对于后人来说,吹捧法家,没有必要,崇拜儒家,也没有必要。重要的还是看对于国家人民有无好处,善则取之,恶则弃之。还是那句老话: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。